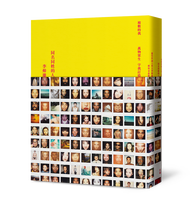|
內文試閱
忽然之間,右先生 「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?」我問運將大哥。 計程車在開往國美館的路上。 「在呀,怎麼不在。我在醫院,我記得有兩次地震。」 「對,還上下動。」 「嘿呀,第二次,我站在路邊,腳底感到有東西在戳,路面上下在動。」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兩點零三分,你在哪裡? 你拿起手機,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,彷彿沒有人類在那一頭。 你要打給誰?你在陽台外推的臥房,腳在地板上,卻像是踩在波面之上,你人在手搖杯裡,上下在搖晃,機遇的手舉起又落下,書架快要倒下,書倒下,CD倒下,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也倒下,砰砰砰砰木板閃過某件家具打了下來,有風,氣流颼一聲地掃到你的腳背,書差點砸中你的頭,抽屜被拉開,櫥櫃門被掀開,玻璃杯撞上瓷碗,傾拎哼楞,鍋子沒掛好被拋了出來,摔了一個踉蹌,金屬的回聲在寂靜裡分外清晰地迴盪著,像水波一浪一浪,吊燈在抖,房子還原為真空的框架,你一點一點加進來這個家的東西,被一件一件地扔回去,你是剛從打撈的手那指縫中逃脫的魚,僅以身免,一丁點的顫動都讓你心頭一震,你家剛好在大樓最高的一層,沒有彈力的四面牆被來回拉扯,一搖三晃,最小的容許範圍之內有最大的晃動,你想到腳底下的樓面非常有可能塌下去,你想逃到門外,漆黑中摸索著找到門邊,你多麼慶幸臨睡之前你並沒有如常地關上臥室的門,但搖擺中你無法移動,地球還在嘔吐般前後抽搐,地要往上擠,天要往下壓,木造的門框可能變形斷裂,你的肉身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所謂大難臨頭,重點就在臨頭兩個字上。橫梁隨時可以壓頂。多麼地切身。後背發涼。巨變來臨的時候,門是阻礙,牆是陷阱,人身是多麼難得的大目標,每一處都可以受傷。這是餘震,幾秒就是一生一世。 但願這一切沒有發生。 長長的沉默。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凌晨一點四十七分。並不很久。之前。你發現你躺在床上,床板在動,往左右擺,像慣常的台灣地震。你從睡夢裡小塊的黑轉移到張眼後大塊的黑,在完全張眼的瞬間,窗外的街燈分明還亮著,隔了窗戶,窗格子的影子像十字架壓在你的身上,然後,你張開眼,世界在眼前消失。你以為像之前一樣,你翻過身,世界就會平復。但是這次沒有。台灣南北輸電的電纜應聲斷裂。時間如你所願地倒了回去,你趕上了第一次的地震。全黑的世界像無知的心智擴大了一切的感官與恐懼。路上有黑暗,地殼有聲。狗在吠。 接下來是總共一百零二秒的撼動還有歷時很久很久的訊息混亂。之後,你才曉得,這一連兩次的地震會被稱為九二一大地震。規模七.三級。 但願這一切都沒有發生。 但南投市武昌宮的柱子折斷,九十度彎腰;魚池鄉日月潭中央的拉魯島面積縮小,月下老人祠崩壞;台中石崗水壩第十六、十七、十八號溢洪閘門斷裂,遠遠看過去像脊椎有三節骨折,水壩潰堤,水是透明的血液;台北東星大樓倒塌,六天後奇蹟地,遭活埋的兄弟在廢墟中被挖出。電力要到了十二天後的十月三日才全面恢復,期間好些地方沒有水,沒有瓦斯。霓虹是菸灰剩餘的紅點,文明被狠狠抖落。震央集集車站的鐵路被嚴重扭曲,這一段路軌後來被移到台中光復國中的校園,那裡的操場被斷層切穿,跑道是剛要捲起就被壓下來的陸地海嘯,永恆凝固了,這地方,兩年後取名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。這些,你當時當然都不知道。 如果時間真的可以倒流。 飛散的沙塵可以重新凝聚為磚頭,瓦礫長回水泥牆的身上,梁柱鋼筋不外露,看不到裡面塞的是空的沙拉油罐,跪下的房子重新站起,六樓八樓從一樓的地面爬起來回到原來的位置,被削去頭顱的大樓一棟一棟地依次逐一站好,牆壁顏面都生回來了,龜裂的無縫無垢,土地被撫平,沒有撕裂,骨牌挺回去,救護車警察軍隊倒回去,巨大的崩塌聲響闇啞了,嘶─轟—轟隆─嘩啦—沙—唰—兵砰—豁啷─啪─喔伊—喔伊混合著人們的呼喊聲統統沒入夜晚,復歸於無,年輕的兄弟還在客廳玩大老二撲克牌遊戲,弟弟側耳一聽,還是尋常的半夜,不知哪裡的小嬰兒在哭叫,媽媽低聲地哄著。沒有後來持續很久的惡夢。沒有來不及見的面,沒有等不及的和解,沒有沒說出口的道歉,或愛,沒有生離死別。 但忽然之間,天昏地暗,世界可以忽然什麼都沒有。歷史沒有如果,命運還是對人丟了石頭。時針停擺,生命像塵埃。二四一五人死,一一三○五人傷,長長的沉默。巨變來臨的時候,你在哪裡,不,他在哪裡?我想起了你,再想到自己,為什麼我總在非常脆弱的時候,懷念你。那一夜,你存活下來了,歷史定格在某張停擺了的鐘的影像,永遠到不了凌晨兩點,但這一刻,你的時鐘還在走,滴答,滴答,無情地走著,非常響亮。意識回來的時候,你拿起手機,黑暗中沒有電沒有燈沒有訊號。你憑記憶找到室內電話的位置。有訊號,但撥不通。所有的成年人都在打電話嗎?千千萬萬戶迫切地在同一根電話線上擠。你想到了他,卻打給了另外的一個他。 到底有沒有所謂對的時間,對的人?還是所有的右先生,右小姐都不過是剛好在你左右可供選擇的先生,或小姐?Right?Now? (你也會這樣嗎?不只一次想哭嗎?愈努力去解釋,愈被誤解嗎?) (你真的確定嗎?找到了你的最愛嗎?還是不好意思再拒絕,就說服自己接受他了呢?) (你真的確定嗎?知道你在做什麼嗎?還是不好意思去承認,就騙騙自己已經很好了?) 台大社會學系教授薛承泰的《台灣地區婚姻的變遷與社會衝擊》論文:「一九九八年因該年為虎年且為孤鸞年,初結婚率降至千分之六.六九,然一九九九年隨即提升為千分之七.八七,二○○○年更達到八.一九,這兩年結婚率上升應和千禧龍年有關;之後又下降。」那千分之七.八七和千分之八.一九決定結婚的人口,到底有多少是因為千禧龍年,多少是因為過了孤鸞年,又有多少是因為那夜裡過不去的一百零二秒? (你真的知道嗎?真的了解你自己嗎?一直這樣地問,你就會開始動搖嗎?) (你真的相信嗎?得到了最想要的嗎?還是為了他們的期望,就把那夢想都變小了呢?) 關係可以有很多如果,但現實只有一個結果。放棄是會上癮的。本來要的沒有通,不確切的虛線卻接通了。機會的斷層,葬身著某個名字,你錯過了自己了嗎? 「九二一的時候你在台中嗎?」 時間快速蒸發乾涸,像很喜歡魚池鄉的席德進逝世也快三十三年了。我把別篇文章的開頭移到這一篇。那是二○一一年,那時候我要去看席德進逝世三十年畫展。生命有時,唯有文字的敘述可以無限地開始。 距離九二一快十五個年頭了,然後將會是第十六個夏天第十七個。 九二一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你,現在可能又變回不認識,或是無從認識。 不思量,自難忘。 |